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病學及現況請見|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爆發兩個月-疫情現況與醫療展望
1最後更新:2020 年 3 月 1 日
2本文所引用有關 2019-新型冠狀病毒之部分文獻尚未經由同儕審查,應對其持謹慎保留態度,部分內容可能與最終結果不符
3文中所指 2019-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 已由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 (ICTV) 定名為 SARS-CoV-2,其引發之疾病由國際衛生組織 (WHO) 定名為 COVID-19。為避免名詞混淆與定名異動,本文將保留文章發布時所採用之名稱。
就在昨天 (2020/1/31) 凌晨,世界衛生組織將去年十二月於中國武漢爆發的 2019-新型冠狀病毒 (2019-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列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這也是繼一九三○年代首次發現冠狀病毒 (Coronavirus) 後的第三次大規模疫情爆發。冠狀病毒是僅次於鼻病毒 (Rhinovirus) 最常造成感冒症狀的感染源,僅有在極少數狀況會在小孩或老年人造成嚴重病情。然而從二十一世紀揭幕至今,已經爆發兩起冠狀病毒的嚴重感染事件:於二○○三年中國廣東省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及二○一三年阿拉伯及中東地區的中東呼吸道症候群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
延伸影音|公視紀錄觀點【和平風暴】│導演:古國威(正版全片)
打開由中國公布的世界第一份 2019-nCoV 定序報告 (NCBI Reference Sequence:NC_045512.2),並用 BLAST 工具進行序列比對就可以看到 2019-nCoV 與已知物種中,與蝙蝠中發現的類 SARS 病毒有將近九成的相似程度,並與感染人類的 SARS-CoV 有約八成的相似度(圖一)。

圖一、2019-新型冠狀病毒序列使用 BLAST 工具的比對結果。圖片來源:NCBI BLAST
雖然 2019-nCoV 與 SARS-CoV 共有一部分相似的基因組結構,然而依目前的分類研究認為該二種病毒應屬不同亞群 [1]。冠狀病毒是正股不分段單鍊 RNA 病毒 (unsegmented, single-stranded (+) RNA virus),也是 RNA 病毒中擁有最大基因組數量的病毒,一般長約 27 至 31 Kb,而 2019-nCoV 基因組長約 29.9 Kb。冠狀病毒的基因組主要紀錄數個必要及非必要的基因序列,包含棘狀蛋白 (spike protein, S)、膜蛋白 (membrane protein, M)、外套膜蛋白 (envelope protein, E)、核鞘蛋白 (nucleocapsid, N) 等。
冠狀病毒的棘狀蛋白

圖二、(左)SARS-CoV 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影像可見冠狀細胞外的突起,並能由棘狀蛋白的上方(右上)及側邊(右下)觀察到突起的三角形形狀。圖片來源: doi.org/10.1007/978-3-642-03683-5_3
冠狀病毒是體型稍大的病毒顆粒,擁有外套膜 (envelope) 結構,外套膜上可見明顯的棘狀突起物,稱棘狀蛋白 (spike protein, S)。該蛋白質造成的凸起形狀也是冠狀(Corona, 拉丁文「王冠」)命名的原因。一個冠狀病毒顆粒約含有 65 個棘狀蛋白,棘狀蛋白負責接合宿主細胞上的各種蛋白質或醣蛋白。經過胞吞作用後,冠狀病毒的外套膜與囊泡外膜融合,使內部核酸釋出於宿主細胞內 [2]。
S 蛋白可以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由三個 S1蛋白構成,下半部則由一個 S2 接壤上方三個 S1(圖三)。也因此 S1 被視為辨認與接合部,在不同冠狀病毒中擁有比較大的變異性,也主宰該冠狀病毒所辨認的宿主受器。相對而言 S2 扮演接合宿主細胞後,拉近病毒顆粒與宿主外膜的功能,因而在 Betacornavirus 或冠狀病毒中都屬擁有較一致的結構。有趣的是,演化上不同病毒株經常出現趨同演化而辨識相同的宿主細胞受器。因此,病毒如何使 S1 序列變異而產生跨物種感染性及病毒如何趨同演化而辨識類似宿主受器仍是病毒學研究中的未解之謎 [3]。

圖三、HKU1-CoV 棘狀蛋白,黃色為三個S1 蛋白與下方桃紅色 S2 接合,灰色為病毒顆粒之外套膜。圖片來源:作者改自 PDB (https://www.rcsb.org/structure/5I08)
SARS 棘狀蛋白接合 ACE2 主導冠狀病毒的感染
相較 MERS-CoV 主要接合 DPP4,SARS-CoV 棘狀蛋白 S1 辨識人類細胞上的 ACE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也有相關研究顯示 SARS-CoV-S1 能夠接合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 上的 DC-SIGN 及其受器 DC-SIGNR [4, 5]。雖然 DC-SIGN/R 不能主導 SARS-CoV 的感染,但實驗顯示 DC-SIGN/R 的競爭或阻擋可以降低 SARS-CoV 感染。有關 SARS-CoV 與 ACE2 以外受器的交互作用仍有待深入研究。
延伸閱讀|避免吞噬-面對伊波拉病毒的新策略
ACE2 於二○○○年被發現 [6, 7],ACE 與 ACE2 都是腎素-血管收縮素系統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中的重要成員。就如 ACE 一樣,ACE2 是細胞膜上的第一型穿膜蛋白質,有巨大的胞外蛋白酶與疏水性的穿膜結構及微小的胞內結構。ACE 負責將胞外的血管收縮素 I (angiotensin I) 代謝為具有訊號功能的血管收縮素 II (angiotensin II)。而 ACE2 則扮演保護角色,進一步將血管收縮素 II 轉為血管收縮素-(1-9)。血管收縮素 II 具有使血壓升高及維持肺部功能的作用,且文獻顯示當小鼠缺乏 ACE2,會造成血管收縮素 II 累積,並透過 AT1R 傳訊導致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syndrome, ARDS) [5, 8]。
值得注意的是,當 SARS-CoV 感染宿主細胞,因為不明原因會使 ACE2 被切除,進而導致血管收縮素 II 累積。這亦可能是 SARS-CoV 而產生肺部症狀的原因之一。
SARS-CoV-S1 主要透過第 479 位點上的天門冬醯酸及 487 位點上的色胺酸 (N79、T487) 與宿主細胞 ACE2 的 353 位點離胺酸 (K353) 接合 [9]。也因此有文獻顯示,曾有案例 [10] 回報輕微症狀及低傳染性的 SARS 感染,該病毒株被發現 SARS-CoV-S1 T487 已經突變為絲胺酸。在實驗模式中,小鼠及大鼠因為 ACE2 的 353 位點由人類的離胺酸改為組胺酸 (H353) 而阻擋 SARS-CoV-S1 接合,使得 SARS-CoV 難以感染小鼠。

圖四、(a)SARS-CoV-S1 與 ACE2 的接合結構,綠色為 ACE2。SARS-CoV-S1 與人類(b)及大鼠(d)ACE2 的作用關係。圖片來源: doi.org/10.1146/annurev-virology-110615-042301
棘狀蛋白 S2 協助拉近病毒顆粒與宿主細胞
當病毒顆粒靠近宿主細胞,SARS-CoV-S1 會辨識並接合宿主細胞的 ACE2 或其他可能的受器。當複數個接合產生,病毒顆粒彷彿帶有吸盤的黏黏球一般貼上宿主細胞,此時細胞將會透過胞吞作用吞入含有病毒顆粒的囊泡。S2 蛋白此時可能會受到酸鹼度變化或是蛋白質型變影響,開始折疊型變,同時間 S1 被可能存在的蛋白酶剝離。逐漸將病毒顆粒與宿主細胞的距離縮短,縮短到達一定程度後會驅使融合蛋白拉開囊泡的磷脂質外膜,並與病毒外套膜融合,釋出內部核酸至胞內 [2]。在流感病毒、愛滋病毒及伊波拉病毒都能觀察到類似的機制,顯示類似機制通用於不同病毒感染中 [3]。

圖五、(b)下方病毒顆粒上的 S 蛋白(綠)逐漸靠近上方宿主細胞 ACE2 (紫)。(c)SARS-CoV-S1 接合 ACE2。(d)S2 逐漸向外摺疊並拉近病毒顆粒與宿主細胞的距離。(e)紅色的融合蛋白接合宿主細胞囊泡外膜。(f、g)胞吞的囊泡外膜被撕開,並釋放紅色的核鞘進入宿主細胞細胞質中。圖片來源:doi.org/10.1007/978-3-642-03683-5_3

圖六、以 2019-nCoV-S1 辨識位致換原 SARS-CoV 辨識位,並檢驗表現不同受器的細胞的感染狀況。結果顯示 2019-nCoV-S1 能夠透過辨識 ACE2 使病毒顆粒感染細胞。圖片來源:doi.org/10.1101/2020.01.22.915660
2019-新型冠狀病毒與 ACE2
為了鎖定 2019-nCoV 的棘狀蛋白的辨識目標,美國國衛院的實驗室以 2019-nCoV-S1 接合位序列取代原 SARS-CoV 棘狀蛋白辨識位序列,並測試表現不同受器的細胞的被感染量。結果顯示如同 SARS-CoV,2019-nCoV 也能透過 ACE2 感染宿主細胞(圖六) [12]。來自中國武漢的病毒學實驗室 [13] 則成功於實驗室中以猴腎臟上皮細胞 (Vero cell) 培養病毒顆粒,並以之測試病毒顆粒對不同物種 ACE2 的感染性(圖七)。結果顯示,包含人類、豬隻、蝙蝠(被認為是 SARS的來源物種)、麝貓(被認為是 SARS 的過度物種)的 ACE2 序列都能使細胞被感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鼠的 ACE2 並未使細胞產生被感染的訊號,這或許提示 2019-nCoV-S1 與 ACE2 的作用位置或許與 SARS-CoV 相似或相同。雖然上述兩個結果都不能排除 2019-nCoV 使用其他細胞受器感染人類細胞,然而卻在第一時間能將 SARS 累積的知識常識應用於 2019-nCoV 的防治。而比較 2019-nCoV 與 SARS-CoV,不僅上述的 479 及 487 位較 SARS-CoV-S1 不同,且被視為與 ACE2 接合的重要位點 442、472 位點皆與 SARS-CoV-S1不同 [11]。
(2020/03/01 更新)隨時間演進,美國德州研究團隊以冷凍電顯技術破解 2019-nCoV 與 ACE2 接合時的結構[14],該團隊採用第一個被發表的 2019-nCoV 序列表現 S 蛋白,並使之與 293 細胞接合。結果顯示 2019-nCoV-S2 相較其他冠狀病毒有兩個使結構更加穩定的突變,同時 2019-nCoV-S1 的機械結構與其他冠狀病毒相似且保留。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2019-nCoV-S1 在 SARS-CoV-S1 被認為重要的位點多處相異,2019-nCoV-S1 仍顯示出高度的 ACE2 接合強度,測得結果約為 SARS-CoV-S1 的 10-20 倍(圖八)。部分過去能接合 SARS-CoV-S1 接合位點的抗體並不能有效接合 2019-nCoV-S1,這可能使部分 SARS 所用材料無法有效利用於 2019-nCoV 中。
延伸閱讀|突破原子級解析度:冷凍電顯異軍突起

圖七、在 HeLa 細胞上分別表現人類 (h)、蝙蝠 (b)、豬隻 (s)、麝貓 (c) 及小鼠(m) 的 ACE2。並使用2019-nCoV 感染,再以偵測核鞘蛋白 (NP) 的抗體染色胞內感染的病毒顆粒。結果顯示僅小鼠 ACE2 未能使 HeLa被2019-nCoV 有效感染。圖片來源:doi.org/10.1101/2020.01.22.914952

圖八、(左)2019-nCoV-S1 與 ACE2 的接合強度約為15nM。(右)2019-nCoV-S1 與 ACE2 接合時的電顯圖片。圖片來源:DOI: 10.1126/science.abb2507
病毒入侵與藥物開發
為了抑制病毒的感染,各種有關抑制病毒顆粒接合宿主細胞的方法仍在開發中。其中策略包含透過抗體阻斷 SARS-CoV-S1 的接合位、以短鍊肽鍊阻斷 SARS-CoV-S1 等。或是透過懸浮的 ACE2 競爭病毒接合位,亦有相關研究已經證明該方法能有效減低病毒的感染。其他方法像是以病毒自身具有 S2 親和性的肽鍊防止 S2 的折疊,從而防止病毒顆粒靠近宿主細胞。該方法已經被使用在愛滋病毒的藥物開發,雖然仍無法在冠狀病毒上顯示類似的抑制效果,但仍有高度的開發潛力。
當然,以上的藥物開發雖然都還在測試或是假說階段,但針對 SARS-CoV 的藥物卻都可能成為對抗 2019-nCoV 的方式之一。其他像是對伊波拉病毒、愛滋病毒或其他病毒的抑制藥物都可能因為針對類似的蛋白質機械原理可能適用於本次的武漢疫情。
最後,由於冠狀病毒共有的 RNA 辨識性 RNA 聚合酶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錯誤率高,使得冠狀病毒具有高突變性,也更易適應不同的宿主,SARS-CoV 就被發現逐漸適應於人類宿主中。因此,2019-nCoV 的突變與各種可能的變化都是必須被時時監測的[15]。
延伸閱讀|老藥新用 – 奎寧如何阻擋 SARS-CoV-2,成為治療 COVID-19 的潛在藥物
延伸閱讀|從基因觀點解構新型冠狀病毒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參考文獻
- Zhu, N., Zhang, D., Wang, W., Li, X., Yang, B., Song, J., … & Niu, P. (2020). A Novel Coronavirus from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in China, 2019.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Beniac, D. R., & Booth, T. F. (2010). Structural Molecular Insights into SARS Coronavirus Cellular Attachment, Entry and Morphogenesis. In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SARS-Coronavirus (pp. 31-43).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Cui, J., Li, F., & Shi, Z. L. (2019).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athogenic coronaviruses.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17(3), 181-192.
- Marzi, A., Gramberg, T., Simmons, G., Möller, P., Rennekamp, A. J., Krumbiegel, M., … & Steinkasserer, A. (2004). DC-SIGN and DC-SIGNR interact with the glycoprotein of Marburg virus and the S protein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Journal of virology, 78(21), 12090-12095.
- Glowacka, I., Bertram, S., & Pöhlmann, S. (2010). Cellular Entry of the SARS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Transmission, Pathogenicity and Antiviral Strategies. In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SARS-Coronavirus (pp. 3-22).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Donoghue, M., Hsieh, F., Baronas, E., Godbout, K., Gosselin, M., Stagliano, N., … & Breitbart, R. E. (2000). A novel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related carboxypeptidase (ACE2) converts angiotensin I to angiotensin 1-9. Circulation research, 87(5), e1-e9.
- Tipnis, S. R., Hooper, N. M., Hyde, R., Karran, E., Christie, G., & Turner, A. J. (2000). A human homolog of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cloning and functional expression as a captopril-insensitive carboxypeptidas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75(43), 33238-33243.
- Imai, Y., Kuba, K., Rao, S., Huan, Y., Guo, F., Guan, B., … & Crackower, M. A. (2005).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protects from severe acute lung failure. Nature, 436(7047), 112-116.
- Li, F. (2016). Structur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s. 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 3, 237-261.
- Li, F., Li, W., Farzan, M., & Harrison, S. C. (2005). Structure of SARS coronavirus spike receptor-binding domain complexed with receptor. Science, 309(5742), 1864-1868.
- Xu, X., Chen, P., Wang, J., Feng, J., Zhou, H., Li, X., … & Hao, P. (2020). 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 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 Letko, M., Marzi, A., & Munster, V. (2020).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ell entry and receptor usage for SARS-CoV-2 and other lineage B betacoronaviruses. Nature microbiology, 5(4), 562-569.
- Zhou, P., Yang, X. L., Wang, X. G., Hu, B., Zhang, L., Zhang, W., … & Chen, H. D. (2020). Discovery of a novel coronaviru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pneumonia outbreak in humans and its potential bat origin. bioRxiv.
- Wrapp, D., Wang, N., Corbett, K. S., Goldsmith, J. A., Hsieh, C. L., Abiona, O., … & McLellan, J. S. (2020). Cryo-EM structure of the 2019-nCoV spike in the prefusion conformation. Science.
- Genomic epidemiology of novel coronavirus (HCoV-19). https://nextstrain.org/ncov
撰文|蔡宗霖
審稿|洪維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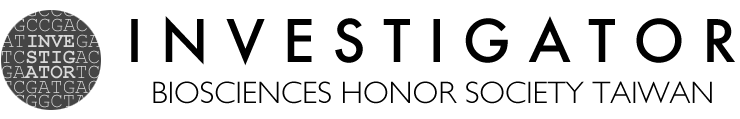







[…] 延伸閱讀│深入 SARS 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上):從病毒入侵到藥物開發 […]
[…] 延伸閱讀│深入 SARS 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上):從病毒入侵到藥物開發 延伸閱讀│又一個來自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2018) […]
[…] 延伸閱讀|深入 SARS 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從病毒入侵到藥物開發 […]
[…] 延伸閱讀|深入 SARS 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從病毒入侵到藥物開發 […]
[…] 延伸閱讀:深入 SARS 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從病毒入侵到藥物開發 延伸閱讀:更有效率的藥物開發概念—建置老藥新用藥物資料庫 […]
[…] 延伸閱讀|深入 SARS 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從病毒入侵到藥物開發 延伸閱讀|從基因觀點解構新型冠狀病毒 延伸閱讀|老藥新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