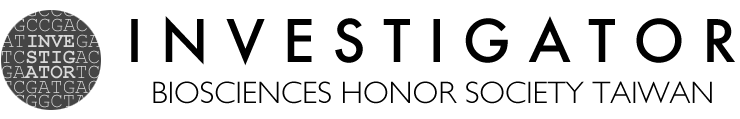過往四十年間,編碼了 p53 蛋白的 TP53 基因,因為與多種疾病及癌症關係密切而受到廣泛的研究。科學家陸續在小鼠腫瘤、人類細胞株與人類大腸癌的樣本中,發現 p53 蛋白具有抑癌的作用 [1]。整體而言, TP53 突變在癌症中的盛行率(prevalence)約 30%,其中該基因突變比例較高的癌症包含卵巢癌、肺癌、頭頸癌、與大腸癌等 [2]。隨著 p53 在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研究得愈發透徹,科學家也探問:在腸道中,常見於 p53 蛋白的突變「熱點(hotspot)」,對於癌症進程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
先前研究指出 WNT 訊息傳導途徑(圖一)可調控大腸癌細胞的增生 [3],而 p53 喪失(loss)則會藉由活化 WNT 途徑,使大腸癌細胞發展出侵略的特性,促進癌症進程 [4]。以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為首的跨國研究團隊 [5],著眼於 WNT 途徑變異誘發的大腸癌,利用 Cskn1a1 (CKIα) 條件性基因剔除(conditional knockout,註一)小鼠模型與帶有 Apc 異型合子 (heterozygote) 的(ApcMin/+ , Apc-multiple intestinal neoplasia)小鼠,探討 p53 突變在小鼠腸道腫瘤發展過程中的生物功能。團隊進一步引入 p53 上的 R172H 點突變,並透過近端(十二指腸與空腸)與遠端(迴腸與結腸)腸胃道的組織分析,比較不同基因型的小鼠之間的差異。

圖一、經典 WNT 訊息傳導途徑(canonical WNT signaling)。缺乏 Wnt 時,Axin、CK1、與 APC 等蛋白形成的複合體會將 β-catenin 磷酸化,使其受泛素化修飾(ubiquitination)而降解。具有 Wnt 時,Wnt 會先與其受體 Frizzled 及輔助受體 LRP 結合,再與支架蛋白 Dishevelled 結合,使 LRP 磷酸化,並招募 Axin 蛋白複合體。β-catenin 在缺乏磷酸化的情況下,便會在細胞中累積並進入細胞核,與 TCF/LEF 結合,活化下游的 Wnt 標靶基因。縮寫:CK1─casein kinase; APC─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TCF4─T-cell factor 4。
圖片來源:Figure 15.45, from The Cell: A Molecular Approach. 6th Edition. 2013. Sinauer Associates: Sunderland, MA. ISBN: (Hardcover) 978-0763739058.
團隊發現,腸道上皮細胞剔除 CKIα (CKIα Δgut)的小鼠腸道環境大致仍維持恆定,而腸道上皮細胞中同時剔除 CKIα 與 p53(CKIα Δgut p53 Δgut)的小鼠則出現嚴重的上皮發育不良(dysplasia)與明顯的增生現象(proliferation)。有趣的是, CKIα Δgut p53 R172H 小鼠在不同腸段的性狀表現則大相逕庭:在遠端腸道的上皮出現高度發育不良與增生的情形,而在近端腸道中則相反:突變的 p53 反轉了 p53 喪失的促癌功能,並減緩了 CKIα Δgut 小鼠所發生的輕度細胞增生與育不良。團隊利用 ApcMin/+ 小鼠作為另一個研究大腸癌的模式系統(model system),也發現了相似的現象(圖二)。

圖二、團隊利用 ApcMin/+ 小鼠與 CKIα Δgut 小鼠,結合組織學與定序數據等分析方法,探討 p53 突變在WNT 途徑變異誘發的大腸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圖片來源: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541-0
為了瞭解 p53 突變為何在近端與遠的腸道中,癌症進程有著截然不同的作用,團隊進一步檢視受到 p53 調控的 WNT 標靶基因(WNT target genes,註二)的表現程度,發現 CKIα Δgut p53 R172H 小鼠近端腸道中 WNT 標靶基因的蛋白表現量皆較低,與 p53 突變株的抑癌作用吻合,而 cyclin D1 與 Myc 等重要的致癌基因表現量則較低,與野生型 (wild type) 相似;在遠端腸道中,WNT 標靶基因的蛋白表現量則甚高。團隊透過染色質免疫沉澱(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分析,結合免疫組織染色,發現小鼠的近端腸道中,p53 R172H 突變可能與 TCF4(T-cell factor 4)與染色質的結合度下降及 H3K4me3 組蛋白修飾的減少有關,進而抑制 WNT 途徑的活化。團隊亦利用類器官(organoid)培養模式,驗證人類突變的 p53 是否與小鼠具有相似的抑癌功能,並發現 p53 突變株具有比野生型 p53 更強的抑癌效果。
在生物學上,近端與遠端腸道最關鍵的差異,便是微生物菌叢分布的程度差異。團隊因此推論:遠端腸道中的菌相,可能干擾了 p53 對於 WNT 途徑的抑制作用。經由抗生素處理後,發現僅 CKIα Δgut p53 R172H 小鼠受影響,遠端腸道的上皮發育情形與腸道構造的分化都有所改善,且 WNT 的活化與細胞增生情形皆減弱。
團隊進一步比較 CKIα Δgut p53 R172H 與其他株小鼠的菌相,卻發沒有明顯不同因推論可能是菌叢的特定代謝物,干擾了 p53 對 WNT 的抑制效果。針對 p53 突變株的空腸類器官施以不同代謝物後觀察類器官的型態(morphology)、增生能力與 WNT 活性變化,發現經由多酚類(polyphenol)代謝物處理的類器官,WNT 活化程度與 CKIα/p53 雙重剔除(double knockout,DKO)類器官相當。其中僅有沒食子酸(gallic acid)能夠顯著改變 WNT 活化程度與細胞增生能力,但對於類器官的型態影響不大。進一步測試發現,環境中具有沒食子酸的存在是阻斷 p53 突變株抑癌作用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在小鼠模型的實驗中也印證了此結果,給予沒食子酸時,近端腸道細胞中的 TCF4 和染色質的結合度及 H3K4me3 組蛋白修飾程度皆有提升,並能誘導 WNT 標基因的表現。由 RNA 定序資料進行生物途徑富集分析(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也發現,WNT 途徑等相關基因表現有最顯著的增加。此外,DNA 複製與 DNA 延長等相關基因表現量亦有增加,推論可能是受到 WNT 途徑活化的影響(圖三)。

圖三、在 p53 突變的情況下,沒食子酸會誘導 WNT 觸發的上皮發育不良與腫瘤進程。實驗結合組織學與基因集富集分析,探討該代謝物對於 WNT 途徑作用的標靶基因之調控作用。 圖片來源: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541-0
這項研點出腸道微生物菌叢對於 p53 突變株在癌症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調節作用,在不同腸段中,因代謝物的差異,使得 p53 突變株有了「抑癌」與「致癌」的明暗兩面(圖四),揭示了在不同腫瘤微環境下,癌症相關基因突變的可塑性(plasticity)。然而,人類的生理機制遠比實驗中的小鼠模式系統來得複雜,了解腸道菌相及其代謝物組成與攝食成分的差異,是否能協助分析疾病進程,其臨床意義仍留待更多研究探討。

圖四、受到微生物菌叢所產生的代謝物影響,p53 突變在不同腸段中對於腫瘤生長有著相反的作用。在近端腸道中,p53 突變會藉由阻斷 WNT 途徑抑制癌症進程。然而,當環境中含有沒食子酸時,突變的 p53 便會失去抑制癌症的能力,並透過活化 WNT 途徑,增強癌細胞增生與侵略的作用,促進癌症發展。 圖片來源:https://doi.org/10.1016/j.molcel.2020.08.021
註一、條件性基因剔除:指在特定組織或器官中抑制某基因的表現,以利專一地探討該基因在特定組織的生物功能。這篇研究以在腸道上皮細胞中剔除了 Cskn1a1 (CKIα) 的小鼠作為模式系統,即 CKIα Δgut 小鼠
註二、WNT 途徑標靶基因:在本篇研究中,作者針對一系列會受到 p53 抑制且與腫瘤侵略特性有關的基因(p53-suppressed invasiveness signature, PSIS)[6] 進行探討,其中有許多是 WNT 途徑的標靶基因(即 WNT 途徑的組成基因與其下游調控的基因),包含 AXIN2、Myc、Cyclin D1、與 CD44。
參考文獻:
[1] Lane, D., & Levine, A. (2010). p53 Research: the past thirty years and the next thirty years.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2(12), a000893. https://doi.org/10.1101/cshperspect.a000893
[2] Bouaoun, L., Sonkin, D., Ardin, M., Hollstein, M., Byrnes, G., Zavadil, J., &Olivier, M. (2016). TP53 Variations in Human Cancers: New Lessons from the IARC TP53 Database and Genomics Data. Human Mutation, 37(9), 865–876. https://doi.org/10.1002/humu.23035
[3] MacDonald, B. T., Tamai, K., & He, X. (2009). Wnt/beta-catenin signaling: components, mechanisms, and diseases. Developmental cell, 17(1), 9–26. https://doi.org/10.1016/j.devcel.2009.06.016
[4] Kim, N. H., Kim, H. S., Kim, N.-G., Lee, I., Choi, H.-S., Li, X.-Y., …Weiss, S. J. (2011). p53 and MicroRNA-34 Are Suppressors of Canonical Wnt Signaling. Science Signaling, 4(197), ra71 LP-ra71. https://doi.org/10.1126/scisignal.2001744
[5] Kadosh, E., Snir-Alkalay, I., Venkatachalam, A., May, S., Lasry, A., Elyada, E., …Ben-Neriah, Y. (2020). The gut microbiome switches mutant p53 from tumour-suppressive to oncogenic. Nature, 586(7827), 133–138.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541-0
[6] Elyada, E., Pribluda, A., Goldstein, R. E., Morgenstern, Y., Brachya, G., Cojocaru, G., …Ben-Neriah, Y. (2011). CKIα ablation highlights a critical role for p53 in invasiveness control. Nature, 470(7334), 409–413.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9673
撰文|陳品萱
審稿|蕭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