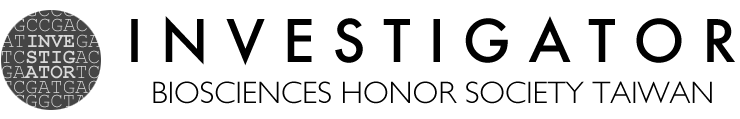靈長類動物的演化過程中,約兩千五百萬年前靈長類動物出現重要的一次分衍發展,類人猿譜系(hominoid lineage)從舊世界猴(Old World monkeys)分衍出來(圖一 a),成為獨立的演化支系。最早的靈長類擁有強而有力的尾巴,幫助它們在樹上更容易抓取食物,並維持身體移動的穩定性。而類人猿從過去棲息在樹上轉往地面上生活,開始直立行走並運用雙足運動,尾巴的功能性便大大的降低。演化至今,大多數猴子及靈長類仍保有靈活的尾巴,但是有相同祖先的「類人猿譜系」乃至於現今的人類,他們的尾巴是什麼原因消失的呢?
所有靈長類的遺傳訊息中都可以觀察到皆有編碼 TBXT 這個基因,TBXT 基因表達的蛋白 — Brachyury,屬於一種轉錄因子,其對於尾巴的發育扮演重要角色 [1],近代科學家認為人類之所以沒有尾巴是因為 TBXT 基因出現突變 [2],但仍對於尾巴消失的遺傳機制了解甚少。本篇文獻研究團隊發現因為跳躍基因 AluY 插入 TBXT 基因中,而影響類人猿不再出現尾巴的特徵。
研究團隊將具有尾巴的猴與類人猿的基因進行比較,發現所有靈長類在 TBXT 基因的第六個外顯子(exon 6)之前皆有出現一個 Alu 跳躍基因 — AluSx1。有趣的是,無尾的類人猿在 TBXT 基因的 exon 6 之後中插入類人猿特有的Alu 跳躍基因 — AluY(圖一 b)。Alu 基因是在靈長類的遺傳訊息中非常典型的跳躍基因(transposable elements),其大量且重複的出現在遺傳訊息中,跳躍基因會透過自我複製的方式跳躍到其他位置,雖然 Alu 基因是內含子(intron),本身不會轉譯成蛋白,且通常不影響外顯子(exon)的表達,但可能會影響基因序列改變或重組。
本篇作者發現無尾的類人猿的 TBXT 基因中插入 AluY,引發了該區域選擇性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的發生,AluY 及 AluSx1 被發現在 exon 6 的兩側附近,互補的 AluY 及 AluSx1 會把 exon 6 包裹起來並黏合形成一個環狀結構,使尚未成熟的 pre-mRNA 在經歷選擇性剪接的過程剃除 exon 6 的基因序列。而出現有別於猴子的 TBXT 異構體(TBXT isoform) — TBXT△exon6(圖一 c)。

圖一 : 靈長類的演化過程,可大致非為無尾的類人猿及有尾的猴。人猿與非人猿在 TBXT 基因上的差異,人猿出現特有的 AluY 基因的插入。 圖片來源: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7095-8
研究團隊利用分子生物學的證據來解釋人類尾巴演化上消失的秘密,作者選用了人類胚胎幹細胞(Human ES cell line)來模擬人類胚胎在早期發育。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編輯的技術,將原本存在於 TBXT 中的 AluY 及 AluSx1兩個基因 分別切除(圖二 a)。TBXT△AluY/△AluY(將 AluY 切除的組別)最終讓 mRNA 在 exon 6 的位置不發生選擇性剪接而維持完整的長度(TBXT full-length),而少部分出現 TBXT 的片段剔除了 exon6 和 exon7 的部分,這解釋了當沒有 AluY 基因存在的情況下 AluSx1 會與在遙遠的互補基因 AluSq2(位於 exon8 附近) 黏合,一併將 exon6 及 exon7 切除。而 TBXT△AluSx1/△AluSx1(將 AluSx1 切除的組別)讓最終成熟的 mRNA 維持完整的長度(圖二 b)。作者推測,AluSx1 會傾向與距離較近且親和力較強的 AluY 黏合達到剔除 exon 6,而較不傾向與 AluSq2 黏合(圖二 c)。另外,結果證實 AluY 雖然是內含子,但是決定了該區域選擇性剪接的重要因素,也凸顯 AluY 在胚胎發育的基因調控之重要性。

圖二 : AluY 及 AluSx1 參與選擇性剪接。 圖片來源: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7095-8
除此之外,研究團隊建立了 exon 6 剔除的異型合子(TBXT)小鼠實驗(圖三 a),進一步驗證在 TBXT△exon6 基因型所生長的小鼠出現短尾或無尾的表現型(圖三 e)。移除 exon6 後,確實讓小鼠尾巴的表現型出現改變。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團隊嘗試將小鼠兩條同源染色體同時移除 exon6 時,會產生一個致命的因素,使小鼠在胚胎的早期發育時期就即停止生長或出生後死亡,而部分小鼠死亡原因為神經管閉合缺陷(neural-tube-closure defects),類似於人類先天的罕見疾病脊柱裂(spina bifida)。這個結果與先前的文獻結果一致,在 TBXT 基因出現突變而造成神經管缺陷或骶骨發育不全等 [3,4]。

圖三 : exon外顯子6 剔除的異型合子小鼠建立。 圖片來源: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7095-8
在先前的文獻表明 TBXT 中的 exon 6 編碼的蛋白序列,包含一部份轉錄因子結合的區域,而 exon 6 的剃除可能會改變原本轉錄因子調控的功能,作者也藉由轉錄體分析(transcriptomics analysis)證實,體外的人類胚胎幹細胞是否保有 exon 6,會影響轉錄的模式,其中的差異可能就是影響尾巴發育的重要調控因素。
這篇研究說明了人類尾巴消失的原因是,因為跳躍基因 AluY 插入到 TBXT 基因,使exon 6在選擇性剪接時被切除,最終導致人類尾巴消失(圖四)。此外,這項研究也證實跳躍基因 AluY 不僅促進了選擇性剪接的發生,也穩固了人類「無尾」的基因型。但是作者認為,在類人猿的演化過程中,仍有其他的基因參與了尾巴發育的調控,所以單單改變人類的 AluY 基因,試圖讓人類重新長出尾巴,其可能性不高。是否有更多基因參與尾巴發育的調控,是未來能探討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類演化歷史中,對於雙腳站立的人類來說,少了尾巴後更適合在生活在地面,也減去了不少的不便。但 AluY 插入 TBXT 基因的現象,可能會影響人類健康,增加了人類罹患神經管缺陷疾病的風險。

圖四 : AluY 插入 TBXT 基因中,是對於人猿尾部消失演化過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圖片來源: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7095-8
Main Article:
Xia, B., Zhang, W., Zhao, G., Zhang, X., Bai, J., Brosh, R., Wudzinska, A., Huang, E., Ashe, H., Ellis, G., Pour, M., Zhao, Y., Coelho, C., Zhu, Y., Miller, A., Dasen, J. S., Maurano, M. T., Kim, S. Y., Boeke, J. D., & Yanai, I. (2024). On the genetic basis of tail-loss evolution in humans and apes. Nature, 626(8001), 1042–1048.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7095-8
參考文獻:
- Schifferl, D., Scholze-Wittler, M., Wittler, L., Veenvliet, J. V., Koch, F., & Herrmann, B. G. (2021). A 37 kb region upstream of brachyury comprising a notochord enhancer is essential for notochord and tai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Cambridge, England), 148(23), dev200059. https://doi.org/10.1242/dev.200059
- Su, H., Zhi, D., Song, Y., Yang, Y., Wang, D., Li, X., & Cao, G. (2024).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ort-tailed phenotypes in animals using mutant mice with the TBXT gene c.G334T developed by CRISPR/Cas9. Gene, 910, 148310. https://doi.org/10.1016/j.gene.2024.148310
- Chen, S., Lei, Y., Yang, Y., Liu, C., Kuang, L., Jin, L., Finnell, R. H., Yang, X., & Wang, H. (2024). A mutation in TBXT causes congenital vertebral malformations in humans and mice.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 Yi chuan xue bao, 51(4), 433–442. https://doi.org/10.1016/j.jgg.2023.09.009
- Kavka, A. I., & Green, J. B. (1997). Tales of tails: Brachyury and the T-box genes.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1333(2), F73–F84. https://doi.org/10.1016/s0304-419x(97)00016-4
撰文|黃宜蓁
審稿|林書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