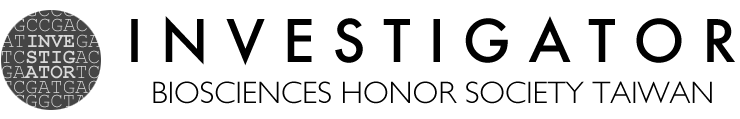1928年,英國的佛萊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在真菌研究中意外發現的青黴素(Penicillin)[1] 相信已經是各位讀者們耳熟能詳的一段有趣故事。抗生素(Antibiotics)這項劃時代的發現開創了醫學大幅進展的契機,至今面對細菌性疾病,抗生素仍然是我們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在抗藥性細菌越來越氾濫的二十一世紀,細菌的抗藥性(Antibiotic-resistance crisis)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威脅著我們的生命,甚至帶來大規模的感染性疾病。抗藥性的演進與廣泛分佈也讓原本一度可治療的感染性疾病變得致命,我們正在經歷一段從抗生素黃金年代(Golden Era)以來前所未見的感染控制難題,同時還有另一項危機伴隨而來:找不到新藥的窘境。
微生物具有發展抗藥性的分子機轉。從古代永凍層中的細菌研究發現多樣的抗藥性基因,這些基因的集合被稱為「抗生素抗藥性基因體(Antibiotic resistome)」[2]。由這些基因可知,抗藥性的產生都是預料中之事。
黃金年代(Golden Era)
抗生素的黃金年代起始於 1929 年青黴素與 1943 年鏈黴素(Streptomycin)的發現[3],我們開始有了對付革蘭氏陽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與結核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方法。1952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Selman Waksman 開發出稱為「Waksman Platform」的抗生素篩選(Screening)方法,開啟了抗生素的黃金年代[4]。透過分離土壤中細菌(Soil-dwelling bacteria)與放射線菌(Actinomycetes)分泌至外界的代謝物來挑選對於病原菌有抑制生長效果的藥物,取代了原本從化學合成物中篩選對細菌有效物質的方法。並以 in vitro 細胞生長抑制(Cell-growth inhibition)實驗作為藥效的佐證並以最小抑制濃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來當標準。
藥物化學年代(Medicinal Chemistry Era)
然而到了 1960 年代中期,使用 Waksman platform 來找尋新抗生素的方法逐漸遇到了一些問題。因為從自然界萃取的抗生素都是相似物,且其本質並非讓人類使用的藥物,所以在人類身上使用時會有大量藥理及毒性(Toxicological)的問題浮現。除此之外,因為是從環境中取得,細菌的抗藥性基因體也容易或已經產生抗藥性。這樣的問題促使了抗生素發展史的第二個重要階段 ─ 藥物化學年代(Medicinal Chemistry Era)。此時的抗生素開發著重在藥物合成的方法,在原有之自然界抗生素基本結構上進行修飾,得到的衍生物有著使用劑量更低、更廣效及不容易產生抗藥性的優點。
抗藥性年代(Resistance Era)
藥物合成時期從 1960 年代開始延續到了 1990 年代的早期。這時,人類的 DNA 重組技術與電腦科技逐漸竄升,基因體學的觀念也促成了現代「Genes-to-Drug」模式的產生[5]。這觀念加速了例如癌症等新藥開發。然而近二十年內,這些新概念與新技術卻沒有促進抗生素的發展。
要理解抗生素的開發窘境,就必須從藥廠對抗生素的篩選(Screening)方法說起。二十世紀的抗生素篩選是以是否能造成細菌生長抑制(Cell growth inhibition)作為指標,而到了現代則以基因是否是非必要(Dispensability)的來決定其編碼的蛋白質能否作為有潛力的藥物標的。現代製藥工業對於必要性基因的挑選仍停留在生長抑制上,沒有考慮毒力因子(Virulence factor)或與感染宿主的過程(Process of infection)有關基因。而且只依賴 in-vitro 實驗來證實,細菌生長環境也都是養分充沛的培養基。這樣的篩選條件可能讓我們忽略了一大群必要性基因。某些基因只有在特定環境下才展現其必要性,而它們不一定將其影響力發揮在細菌的生長上[6]。
現代的藥物工業多半以 Target-based screening 來取代 Cell-based screening。Target-based screening 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可用的標靶,卻都是未知功能的蛋白。若我們缺乏對該蛋白功能的認識,我們就無法選擇相應的分析方法來驗證其能否實際應用至臨床上。此外,過去成功的抗生素多半是藉由多種機轉來達成殺菌或抑菌的效果,並不是只針對單一標的蛋白的抑制。例如,β-lactam 類抗生素,其作用不僅是抑制 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s(PBPs) 如此簡單 [7]。
除了必要性基因和 Target-based screening 的問題之外,抗生素能否成功穿透細菌的障壁或是不被排出也同樣重要。從自然界篩選的抗生素多半生物活性(Bioactivity)佳但通常為已知結構的藥物;而 Target-based screening 的藥物生物活性差但可容易找到新種標靶蛋白。
未來的方向: Narrow-spectrum Era
現代抗生素新藥開發的困境是未來十年內衛生官員與製藥產業需要解決的問題。各國政府透過政策來促進抗生素的開發。美國 FDA 僅根據臨床第二期試驗便讓 Ceftazidime 及 Avibactam 合併的療法通過。GAIN(Generating Antibiotics Incentives Now)法案也獎勵了抗生素的開發[8],在歐洲也有類似的補助如: Innovative Medicines Initiative 來鼓勵製藥公司開發新一代抗生素。
有效、安全且廣效的抗生素如今已經難尋。黃金年代與藥物化學工業帶給我們帶來的優勢,未來可能不再復見,以後也越來越少廣效(Broad-spectrum)抗生素可用。在這個生物技術發達的年代,抗生素必須從廣效逐漸走向精準、專一窄效(Narrow-spectrum)的方向來面對當前抗藥性叢生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期許窄效、細菌屬專一性甚至是種類專一性,針對各單一菌種專有的細胞合成代謝路徑的非傳統類抗生素將會大行其道來對抗排山倒海而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細菌抗藥性浪潮。

參考資料:
[1]https://goo.gl/WHjuMV
[2]https://goo.gl/k45Xnh
[3]https://goo.gl/knaXLv
[4]https://goo.gl/1an7mr
[5]https://goo.gl/HV4ZYj
[6]https://goo.gl/zSC42j
[7]https://goo.gl/KHqAVx
[8]https://goo.gl/GCTZJm
圖片來源:
https://goo.gl/sU5kzX
撰文|姚京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