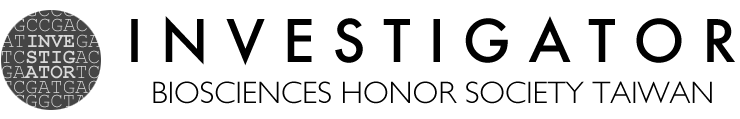和許多生命科學的學者不同,顏雪琪老師年輕時並沒有想過投入生命科學研究。高中時,老師比較感興趣的其實是化學和藝術,但在父親的影響下,大學進入台大動物系就讀。由於有機化學表現良好,還被當時授課的陸天堯教授邀請進入實驗室做有機合成。之後又進入宋延齡老師的免疫實驗室見習。
畢業後,老師憑藉優異成績直升台灣大學分子醫學所碩士班(當時有保送制度),並進入呂勝春老師實驗室從事真核細胞轉錄調控蛋白質之研究,接受兩年的扎實技術訓練。
博士研究時期
老師在擔任一年研究助理後申請入紐約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紐約大學是全美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學院涵蓋各個領域,同時也是學費屬一屬二昂貴的學校;校舍分散在紐約市內,只要看到掛有紫色旗子的建築便是紐約大學的校舍,校園、城市合抱。不過,起初抱著旅遊心態來到紐約的欣喜,很快就被現實沖淡。
老師博班起步時承受不小的壓力,除了要克服語言障礙、熟習陌生環境,還必須承擔授課的義務。美國的全額獎學金(full scholarship)分三種:RA(Research Assistantship)、TA(Teaching Assistantship)以及 Fellowship;大多留學生拿到的獎學金屬於 RA 或 TA ,取得 TA 獎學金就必需擔任課程助教。老師回想起來,當時被安排擔任比較解剖學的助教,要以英文教授拉丁文的專有名詞真的備感艱辛。相較之下,實驗技術反而是一開始不用擔心的部分 (美國許多人大學畢業即攻讀 PhD,實驗經驗不足算是常態)。
擔任助教外,博班第一年還要進行輪轉(rotation)。老師原本已經決意進入研究基因轉錄調控的實驗室,可以接續碩士熟習的生化研究領域,並使用相近的研究材料。輪轉時另外選擇研究酵母菌和果蠅的實驗室只是因為規定,老師笑著說,實際上這兩間實驗室是她當初認為絕對不會去的,抱持著這輩子要做這些事也就只有這次機會的心態;但是一個實驗室是否適合自己,不是只和研究主題相關,實驗室的風格、老闆的個性等都很重要,輪轉時在每個實驗室工作二到三個月的本意就是要學生充分理解這些細節,再做選擇。老師回國後發現國內的學生傾向一開始就選定指導教授,考慮到博班短則四年長則七年,且會影響人生走向,輪轉的權利務必要把握。
經過再三考慮後,老師進入了 Eric C. Chang 的酵母菌實驗室。該遺傳學實驗室主要以裂殖酵母菌(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為生物模式,透過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研究基因突變與細胞存活之關係。老師會選擇進入較陌生的遺傳學實驗室,除了考量到實驗室的風格外,和研究方法的性質也有關。酵母菌的實驗操作較簡單,從構思到完成檢驗的週期較短,因此可以花較多時間在思考研究策略和實驗設計;相反的,有時候研究技術困難、操作繁複,反而沒有太多思辨的機會。[1]
博士後研究
博士畢業後,老師決定留在學界做博士後研究(Post-doctorial Research),增長學術實力在研究的道路上繼續邁進。老師選擇研究室的首要標準是興趣,在廣泛的搜尋並獲得數個正面的回應後,顏老師最後鎖定兩間實驗室,分別是 Susan Lindquist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以及 Stephen J. Elledge 在貝勒醫學院的實驗室(後來移至哈佛)。
Susan Lindquist 的實驗室主要研究蛋白質摺疊相關的問題如 Prion、伴護蛋白、熱休克蛋白,團隊擁有物理、化學、生化等各領域的專家,以不同的方法針對同一個主題研究;Stephen J. Elledge 的實驗室則恰好相反,實驗室多達三十位研究人員都有方向各異的題目,團隊開發了很多研究工具,研究人員開發並應用這些工具解決各自的問題。簡單地說,Susan Lindquist 實驗室的題目很明確,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Stephen J. Elledge 的實驗室可以提供各種工具,需要的是問題。
顏老師認為,在生物學找一個題目不難,有許多重要問題和有趣的現象等待研究,但問題無法解決往往是因為缺乏工具。因此雖然對 Prion 極有興趣、Susan Lindquist 實驗室也非常友善,老師最後選擇 Stephen 的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這也符合老師的自我期許,老師希望未來在面對挑戰時,會成為一個有勇氣建立新方法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會被既有工具的不足囿限。
老師的博士後研究是希望開發一個工具,能夠偵測活細胞全部蛋白質的穩定度(GPS, Global Protein Stability)。不過,大家的研究主題不同又都很創新,無法得到太多支援,所以即使資源豐富仍然承受許多磨難,曾經長達三年試遍各種方法都沒有結果。在這段充滿挫折的時期,老師理解到研究之外仍要有生活[2],也培養了繪畫的興趣,工作以外的調劑不僅維護心理的健康,有時也對研究有所啟發;現在老師每年都會有一段時間拋開工作出去旅遊,此次訪談恰巧就在老師前往奧斯陸前夕。生物研究往往長達數年且實驗有很多中間步驟,所以研究者往往會深陷在小環節,看不到大的格局、過度在意當下面臨的失敗;若能適時的放鬆,像畫畫一樣退一步看看計畫的全貌和初衷,會更有利於解決問題。老師後來不但成功開發了GPS,還進一步利用它發現了SCF 泛素黏合酶 (ubiquitin ligase)的標的蛋白質,登上 2008 年的[科學](science)期刊。
中研院分生所時期
老師於2010年回到台灣,在中研院擔任助理研究員。繼續改善GPS 並利用它研究蛋白質更新(turnover)等蛋白質網路的調控,並研究建立全蛋白質調控方式的高通量技術。
國內環境與美國的差異
顏老師在波士頓感受到最明顯的差異,是國外的研究者、學生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們以充滿熱忱的態度尋找自己想解決的問題,而不像在國內很多學生僅僅是服從老闆的指令,或只追求代表成就的指標。老師回想當年 Stephen 實驗室內一群同樣對研究充滿熱忱的人彼此交流、提出瘋狂的創意,這樣能夠彼此激盪的環境讓人非常開心。
另外,美國研究計畫通過率遠比台灣低,固定的公共資助也比較少,拿不到計畫致使實驗室關門是常有的事。老師博士班三年級時實驗室就遭遇過經費不足的困境,連蓋玻片、牙籤都要回收,面臨是否要長期停工的抉擇。這和國內平均計畫經費較低,通過率較高的環境很不同。
撰文|謝善棋
編輯|魏子堂